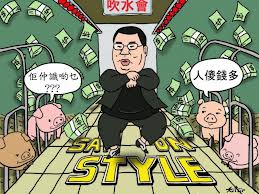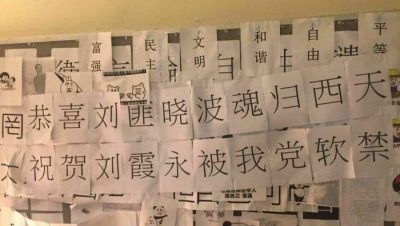博鰲亞洲家庭教育專家學術論壇成果分享
——同一個家,同一個夢
筆者以十多年家長義工和親子教育工作者的身份,有幸應邀代表澳門出席博鰲亞洲家庭教育專家學術論壇,與來自中國、韓國、日本、以色列等十個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兩千名家庭教育導師和代表分享了家庭教育的方法和理念,並獲主辦方頒授“亞洲家庭教育貢獻獎”。為了履行此獎項給予的使命,筆者將透過系列文章與澳門讀者分享會議成果。率先登場的是有關會議主題的思考。
同中有異
本屆論壇以“同一個家,同一個夢”為主題,據我個人了解是在世界大同的追求下,不同地區的家庭都懷有相同的夢想——建構和諧、幸福、美滿的家庭。因此,分別來自塔吉克斯坦、沙特阿拉伯、以色列、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中國內地、台灣、香港、澳門等專家透過主題演講與台下兩千多名內地家庭教育導師交流經驗,期望實現家庭和諧、幸福、美滿的夢想。其中又以三個地區的教育體系差異較大:
以色列教育部家庭教育督導歐仁 · 斯達力克的演講《幫助孩子成就自己》中指出,幫助孩子成功的父母包括以下特質:
1.重視愛與關懷
2.建立生活流程
3.重視本土文化(與以色列文化的聯繫)
4.學習生存技能
5.允許孩子失敗
以色列猶太民族是世界公認的優秀民族,全球一千三百萬猶太人只佔世界人口的千分之二,卻取得了百分之二十九的諾貝爾獎;以色列是個新興國家,在缺水缺地的客觀環境下,仍然成為世界強國,如此成就與家庭教育的關聯為人所關注的。在歐仁 · 斯達力克的演講中,最突出的是“重視本土文化”的部分,以色列家庭從小就開始建立孩子的身份和文化認同,形成了他們自強自立的傳統。而在允許孩子失敗方面,以色列人認為:“失敗”是與成功更靠近一步,他們會讓孩子主動探索,並勇於面對失敗為榮。而一直致力讓猶太教育在中國落地生根的中國教育家周穎同時指出猶太家庭教育的優點是“不把孩子困在狹小的盒子裡”,猶太家庭教育給中國帶來以下的啟示:
1.真正的因材施教在家裡
2.相信家庭的力量
3.母親是保護者、陪伴者、教育者。
4.父親是孩子大腦的塑造者
印度阿育王大學創業中心發起人和總監普利亞克 · 納拉揚教授在其《如何在家庭中把握好未來及印度家庭教育》的演講中介紹了印度如果透過家庭教育平衡十年如一日的學校教育模式,因應社會發展的需求,他以五個C來歸納家庭教育的重點:
Communication 溝通
Collaboration 協作
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性思維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創造性解決問題
Contra-Dsciplinarity 反學科(重視孩子的綜合能力)
無獨有偶,印度家庭教育同樣重視家長如何協助孩子“處理失敗”的情緒,他們認為,失敗僅僅意味着第一次學習。作為家庭教育工作者,我們必須讓孩子知道學習不是機械地完成任務,而是隨時隨地的終身學習歷程。
三天的會議中,各國代表都為我開啟了新的視覺,而最令筆者感到震撼的,竟然是有關中國傳統的家庭文化,會議稱之為“家風”——家庭或家族世代相傳的風尚、生活作風,是給家族後人樹立的價值準則,內容包括:精神風貌、道德品質、審美格調和整體氣質的家族文化風格。比較難忘的是中國人生科學學會家庭教育科學研究院林青賢副院長所提到的中國幾大世家,包括:錢氏(錢鍾書世家)、諸葛亮、朱柏廬、黃庭堅等,他們的家訓都各具側重點,但都離不開成人、成才、成事三個方面,而當中大都源自人所熟悉的中國傳統哲學理念。回應前文以色列代表的發言,家庭教育的重點之一是“重視本土文化”,因為只有從小開始建立身份和文化認同,我們才能在最適合自己的文化土壤中孕育新苗,如何承先啟後,做到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與時俱進,將是我國家庭教育發展的核心議題。
異中有同
在筆者看來,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台灣、香港、澳門等地,都有着相類的社會背景和文化特質,其中又以日本的家庭文化更為重視生活細節,如:生活作息和人際互動等,各地代表都圍繞着自己的關注點進行演講。在同中有異的家庭文化中,我們看到了相同的本質,那就是親情的重視和生命的承擔。誠如多位講者所言:家庭教育是全人教育的開端,只有培育具有真、善、美追求的新世代,世界大同的願望才有機會實現。(一)
摘自澳門日報
http://macaodaily.com/html/2018-04/05/content_125598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