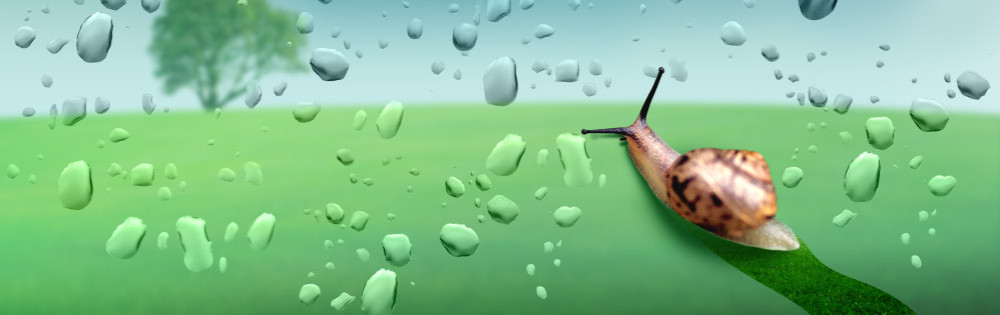我用骨頭掘地基,用我嘅血同水泥溝埋一齊……我愛你,你知道!
【摘自:教育劇場《骨籠》;原著編劇:Geoff Gilliam;劇本翻譯:周杰成;草莓田藝術教育工作室;二○二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喜歡做帶領者還是跟隨者?”劇場開始的時候,我們玩了一個小遊戲,主持人這樣問我。
一直以來我都以為自己喜歡做帶領者,但那一刻,我竟然比較喜歡做跟隨者。大概因為,我沒有特別想去的地方,我信任帶領者,而跟隨者被動的、不可預知的體驗也充滿快感。
我覺得《骨籠》是一個講述帶領者和跟隨者的故事;我覺得帶領者對跟隨者的愛是扭曲的愛;我覺得跟隨者用病態的方式感恩……為什麼是“我覺得”?因為不同觀眾似乎有不同的感受,觀眾一邊觀看劇場,一邊討論“拯救者偷到了鎖匙,打開了大門,並給跟隨者一把逃生的刀子,跟隨者要不要離開”。以白羊座的性格,我是不能夠被操控的,然而,站在人生交叉點的一刻,我猶豫:面對陌生的拯救者,以及未知的容身之地,有種難言的恐懼……
“戰爭再可怕也是演習,這就是我們的世界。”帶領者說。“不可以放棄自設的戰爭嗎?”我不理解。“我不會離開!雖然失去自由,沒有尊嚴,但這是我的家。你不愛家庭嗎?”跟隨者問。“我愛家庭,但不可以同時擁有自由和尊嚴嗎?”我不滿。結果我選擇放下求生的刀子,頑強地站在原地,等待帶領者的覺悟,或是以死亡換取靈魂的自由。
“一把新的刀子是用很多成本換回來的!”拯救者說。我感恩其努力,然而,為什麼不可以選擇站在原地?為什麼必須放棄才能擁有?我不服氣!我相信只要放下傳統觀念的約束,跟隨者也能夠自主——向無理的操控say no,並感受被帶領的喜悅!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2-09/30/content_162474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