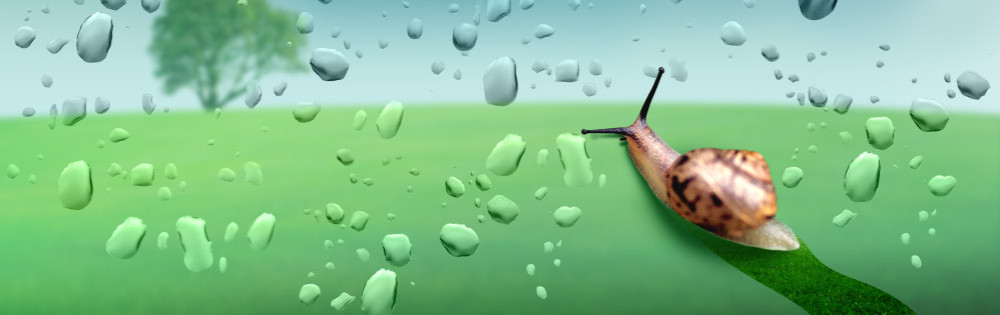鳥兒想從蛋中出來,蛋是鳥的世界,想誕生者必須破壞一個世界。
【《德米安》,作者:赫尔曼 · 黑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
十幾天了,你無法想像,平日驕生慣養的孩子,可以餐風露宿,在不同的咒罵和打鬥聲中堅持下來。而他們當中的很多人,更因此和家人決裂,以換取理想,作家阿果在其作品中描述“一場運動,兩代裂痕,不知擘開了多少家庭”。孩子們大概也是想家的,於是有心人發起“給爸媽的信”行動,鼓勵年輕人掏出真心,親筆疾書,並用手機拍下父母讀信的照片,但真實的情況卻是,許多人連將信親手交到父母手上的勇氣都沒有。看着井然有序的路邊小社區,還有充滿學習氛圍的臨時自修室,誰都會感動,但回歸真實的世界,又找不到那條可以回家的路。也許,不是孩子不想回家,也不是父母不肯原諒,而是找不到路可以通向彼此的心。
眼前的景況,不免讓我想起故事《德米安》。出生並成長於“光明世界”的辛克萊,偶然發現截然不同的“另一個世界”,那裡的紛亂和黑暗,使他焦慮困惑,並陷入謊言帶來的災難之中。這時,一個名叫德米安的少年出現了,將他帶出沼澤地,從此他開始走向孤獨尋找自我的前路……引文是書中有名的譬喻:要想獲得新生,就必須衝破這些懷疑和痛苦,才能看到一個新的世界,蛻變成一個新的自我。
那群單純的孩子就是辛克萊,他們完全無法理解另一個世界中的種種。他們以為,只要破壞蛋殼,就可以起飛了,卻忘了自己不是鳥,也不能飛——有些沼澤,再難熬也得花時間走過。傳說中的德米安會否出現?哪個方向可以走向光明?蛻變是個變天換地的過程,還是個自我探索的經歷,沒有人知道。到“戰地”探訪的學生道:現況的不調和是因為“大同”與“小康”的分歧。但其實,當下的追求真的就能成就大同世界?離開“外國更圓的月亮”的時候,我就找到過答案:世上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成就生命的全部,在痛惜自家不完美的同時,我更留戀文化的根,故土的情,親人的愛,以及社會的尊重和互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