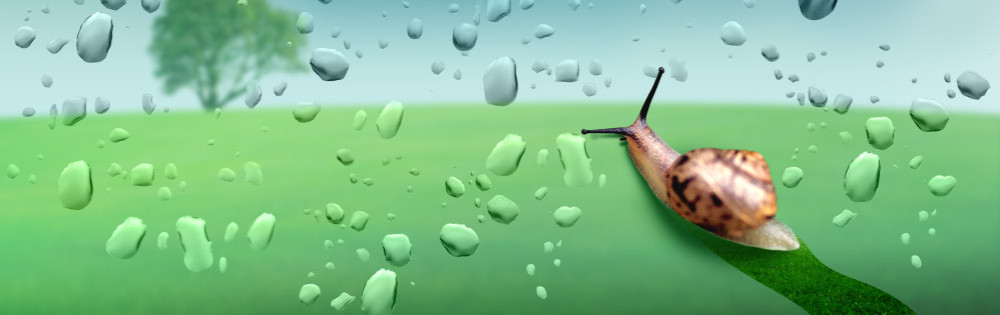訪談中亦發現,受訪者在處理壓力及遇到壓力時的反應亦相當類似,大部分受訪者在處理壓力時會選擇尋找虛擬空間或創造儀式感治癒自己,如“寫寫Blog”、“把心事摺成星星許願、好好儲起”等。
【摘自:《澳門中學生精神健康現況調查(二○二三年)》,澳門學聯升學及心理輔導中心,二○二三年十二月】
英國雜誌《經濟學人》統計數據表明(二○二○年),在全球範圍,自殺已經成為十五至二十九歲人群的第二大死亡原因,其中少年自殺人數為世界首位。中國北醫兒童發展中心發佈數據顯示,內地年均約十萬少年死於自殺,平均每一分鐘就有二人自殺致死、八人自殺未遂。青春本是美好的,為何卻心生厭倦?我想那大概是基於青少年身心發展不平衡,讓他們更容易形成心理障礙之故。
針對青少年問題,政府、學校和民間都做了大量工作,但患有心理隱患的人多數是不會或不懂求助的,何況是年少的孩子?因此家長成為了主要求助者,家庭教育課程、心理諮詢服務等應運而生。作為青少年父母,我因利乘便加入其中,每天在媒體接觸大量案例:我家孩子躺平了,遊戲成癮了,“○○後”的奇葩怪獸全國統一培訓的……
其實新一代的奇葩怪獸父母也不少,但我們很少在正式媒體聽到青少年控訴的聲音,一如上面的調查:青少年傾向自我療傷。如何讓青少年的心聲被聽見?是我研究的方向,因此我選擇以“青少年”為主體的教育現象學作研究,把自己青少年時代和父母衝突的體驗寫成故事,輕鬆地總結出成為智慧父母的建議。研究完成後,我把成果在青年社團發佈,並計劃給青少年寫建議,方才發覺親子溝通方式很難反向呈現,要求青少年同理父母自然不容易,要父母接受“只是被理解而非服從”相信更難。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4-03/08/content_173988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