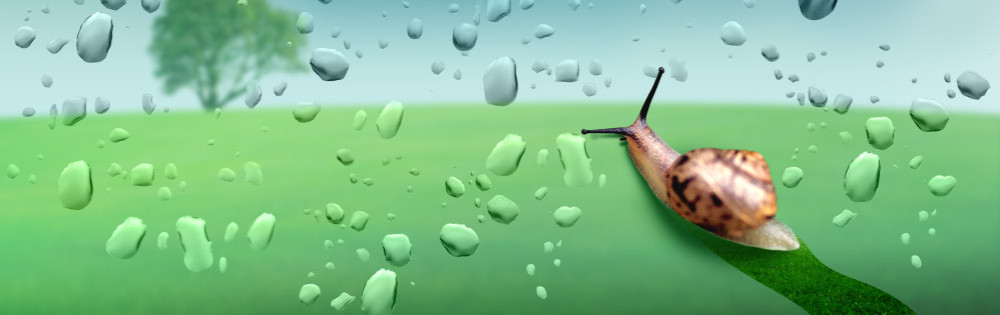“孩子,你開心嗎?”是我早年學回來的育兒秘技,用意是讓孩子知道父母關心其感受,若然真的遇到不快的事,可以及時給予指導和支持。小時候受了委屈,進門就滔滔不絕的孩子,到了青春期,天真無邪的臉卻變得陰晴不定。“孩子,你開心嗎?”這話顯得幼稚,但看到孩子愁眉不展時,我還是會按捺不住地問“孩子,你不開心嗎?”,哪怕最後只收回一陣冷待。
“為什麼總愛問人家開不開心,不覺得這樣子會令人尷尬嗎?有需要幫忙自然會說。”朋友批評我。說的也是,長大成人了,開心與否,父母都幫不上忙,不說為妙。直到前幾天,讀到澳門基督教青年會發佈的有關青少年與親子關係的調查結果“本澳家長多認為自己管教方式屬於開明民主型,子女則認為父母屬於忽視冷漠型,反映親子雙方認知差異大”。再次讓我感受到關心孩子情緒的重要性,哪怕他們總是擺出愛理不理的樣子。
如何既表達關心,又不致於讓青少年反感?我為此組成了專家小組進行研討,收回以下小秘技:先“眼到”,再“手到”,最後才“口到”。說話力量有限,我們先要觀察孩子的生活小節,再詢問具體情況,例如:媽媽最近發覺你無精打采,是功課有壓力嗎?如果說中了,或者會成為他們傾訴的契機,而即使反應冷淡,父母也可以借機表達簡潔的關心(切記要簡潔,青少年不愛長篇大論);手到是指行動,無論多晚未歸,家長也可以給孩子留碗熱湯 / 他喜愛的小點心;遇到挫敗時,不要急着說教,先來個熱情的擁抱,或是“拍膊頭”打氣,讓孩子知道無論如何,父母一直都在,等心情平伏了,再總結教訓也不遲。
《二〇二二年國民抑鬱症藍皮書》指出,十八歲以下的抑鬱症患者佔總人數的百分之三十,其中百分之五十為在校學生,而家庭關係是當中重要的壓力源。處於羽翼未豐的階段,青少年起飛並不容易。“孩子,你不開心嗎?”願你永遠記住:世界只關心你飛得高不高、遠不遠,唯有我在乎你飛得累不累。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3-02/28/content_165706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