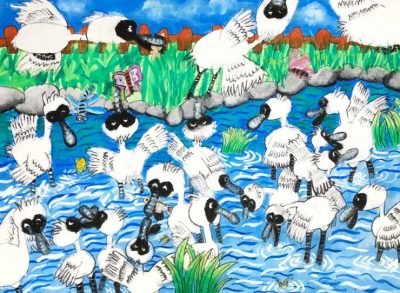3D數位分身是利用生成式AI為核心,即時把圖像去背,將照片快速轉換成人物模型,呈現細微的動作,還可以開口說話。
【摘自:〈AI分身!“數位人類”變網紅、照片變3D人物模型〉,李采穎、李承祐,二○二四年一月十日】
讀者見我最近熱衷在內地做直播和短視頻,都一股勁教我如何更好地謀利。其實我沒想過自己真的能賺錢,因為內地的播主太厲害了,他們可以天天做直播、出視頻。而“羊豬老師”還要上班,每周能做一場直播已經好勉強。於是朋友教我如何找AI寫段子,甚至找AI替身代言。
替身可以是優化版的自己,要美顏可美顏,要瘦身可瘦身,如果對自己不滿意,還可以換一張臉,要美貌有美貌,要身材有身材,不但發音準確,還有不同氣質:知性名家、可愛甜姐、傻氣小孩子,應有盡有。世界閱讀日當天,我隨便找了一張傻氣照片,配上傻氣小孩子的聲音發佈視頻,雖然臉容有點扭曲,說話不夠自然,但看着還是相當有趣。
“會不會真的用替身賺錢?”暫時不會吧。目前來說,我和人分享的最終目的是學習,首先是練習普通話,繼而督促自己每周閱讀、思考和分享。既然AI也可以做直播,還學習什麼?完美的AI可以代替你做事,卻不能代替你生活。我們學習的最終目標不是做事,而是做人。我們透過學習增長知識,透過生活實踐悟出道理,讓自己可以更好地活着,而不是求取更大的成就和賺更多的錢。
我有時也會用AI寫作,好奇它到底會如何解讀,但AI不能代替我思考。我們不需要比較AI和自己誰做得更好,因為只要有能力操控工具,一加一會大於二。如何成為一個能獨立思考,有足夠的智慧運用工具的人,才是我們學習的方向。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4-04/26/content_175075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