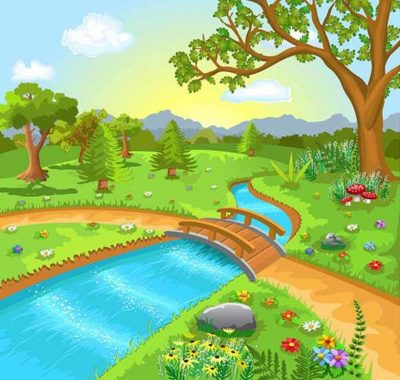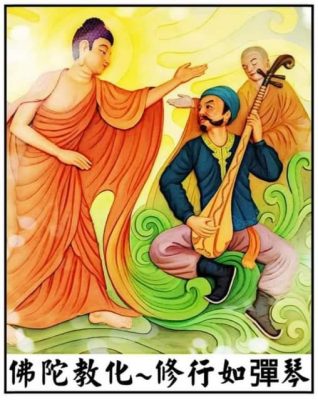一位哈佛大學中國畢業生(蔣雨融)在畢業演講裡呼籲在分裂的世界中尋求團結……有人表示被感動到落淚,但是也有人指出她的精英背景無法代表大多數中國學生。
【摘自:〈哈佛大學中國畢業生蔣雨融演講〉,黃思琪,二○二五年六月三日】
蔣雨融的演講在語言節奏、表達技巧和內容構建上不算上乘。然而,當我在網上看到對她語音、內容、品格、家世和外貌的指責時,不禁思考:畢業演講的真正意義究竟是什麼?
畢業演講應是學生在知識殿堂中自由表達的一個機會。蔣雨融在台上分享她的感悟與呼籲,這聲音本質上是她個人的心靈窗口,展現了她對世界的理解與期盼。這或許能引起某些人的共鳴,但也可能無法觸及一些人的心靈,這正是聽與說之間的常態。在東亞地區,畢業生的致辭往往需經過嚴格的審查與修改,甚至有專人陪伴學生演練。作為演講教練,我常常擔任陪練角色,若認為學生的內容不理想,大可更換對象,而非要求學生照本宣科。讓學生發表忠於自我的演講,這是對人的基本尊重。演講的優劣不應成為惡意攻擊的理由。
可悲的是,現實的喧囂常常淹沒這份純粹。當講台置於國際政治的陰影之下,當一位年輕人的聲音被粗暴地推上“代表”的位置,內容便很容易被扭曲。
蔣雨融在演講中呼籲尋求團結,卻不幸成為網絡上攻擊的焦點,這正是她呼籲的最刺眼的現實映照。世界的分裂不僅存在於國與國之間,更深植於人心,悄然滋長於每一次對異見的輕蔑、對“非我族類”的標籤化否定,以及對個人尊嚴的漠視。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s://www.macaodaily.com/html/2025-06/06/content_183694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