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插圖取取自澳門日報 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1-11/19/content_1557806.htm
一
“我們今天來這裡幹什麼?”
“學習……”
“聽不清楚!有氣無力的,你怎麼幫助孩子?再來!你們來這裡做什麼?”
“來學習……”
“重要的事情要說三次!”
“學習!學習!學習!”
“是的!我們來這裡學習,我們首先要找回生命的能量,我們自己沒有能量,孩子怎麼會有能量?對不對?”
“對的!”
“大聲……對不對?”
“對!”
“我們以身作則,上課能不能玩手機?”
“不能!”
“能不能?”
“不能!不能!不能!”
談到不玩手機,家長情緒高漲,恨不得手機這公敵粉身碎骨。
“說得對!手機這東西是世紀毒藥,誰玩手機,誰就被毒害,你們做父母的,還玩不玩?”
“不玩!不玩!不玩!”
“正確!不想孩子玩手機的話,你們便要先做個好榜樣。”
這樣的呼籲很有效,為期兩天的課堂,基本上沒有家長把手機拿出來。大家對燃點生命的能量一說似乎充滿熱情。
“好!現在我們要請三位家長出來和導師拍照。誰來?”主持人接着問。
台下家長猶豫了。
“我來!”一位勇士舉手。
“歡迎這位家長,拍這張照給誰看?”
“嗯……放朋友圈吧。”台下觀眾笑了。
“放朋友圈給誰看?”
“給老公?”
“還有呢?”
“給孩子看!”
“說得對!就是要給孩子看。你要他努力學習,你努力嗎?你家孩子看到你努力學習,這就是身教!明白嗎?”
“明白!”家長齊聲答,然後爭相出來和導師拍照,並立馬發給孩子。一如主持人說“每個人眼中都充滿生命的能量”。
二
叮、叮、叮……在另一間課室內,一群青少年在聽課,他們和父母的生命能量相反,每個都沒精打采樣的,即使導師用充滿生命能量的呼喚鼓勵着他們做體操。
“什麼聲音?”導師立馬停下正事。“你們聽到了嗎?那是生命的呼喚,就像懷胎十月的孩子在媽媽子宮內準備出生的聲響!”導師的奇異比喻懾住了這群少年的神經。
“是什麼聲響呢?”大家一時間靜了下來。
“什麼生命的呼喚?不過就是我媽和導師的合照傳過來,這種把戲又不是第一次。”一位神態自若的“老司機”少年說。
“啊⁈這同學真有悟性。既然爸媽一番好意,你們總得珍惜……想想你們幼稚園時候做的小手工多簡陋,爸媽不一樣掛在身上或是廳堂嗎?”導師果然是導師,他很熟練地運用青少年相處之道的方程式:(不動氣+厚顏)+(接住情感+表示認同+生活化比喻)=引發同理心。
在場的少年心裡或許未盡同意,但至少不反抗,多數人都按其指示拿起手機一睹熟悉的臉孔。看着父母久違的溫和笑顏,如風雨後的彩虹,孩子們動容了,紛紛報以傻笑。
“被爸媽的好學不倦感動了吧?覺得是的舉手看看!”
場中只有幾隻手舉起來。
“年輕人,別害羞!讓我們拿着手機大聲說:我愛你!”
場中飄來細碎的聲音。
“大聲點!有氣無力的,我們準備去吃飯了,趕緊說……要不然留下來逐一拍攝,單獨對父母講:我愛你!”導師呼籲。
誰想留下來拍攝單獨的誓言呢?少年們迫於無奈在台下說“愛你!”完事。而這些場面落到經驗老到的導演手中,剪接成完美無瑕的親子生命連結微電影,比大台綜藝節目的導演還要出色。
“你剛才真的感動了嗎?”子薇問旁邊的少年,他們相識於微時,母親是閨密。
“哈!難得一場大龍鳳,總得給點面子吧!”文光說。
“英雄所見略同!”同組的少年豪興奮和應。
“這場大龍鳳可是不便宜,是我二十節小提琴課的價錢!”子薇覺得不值。
“那麼貴嗎?”文光覺得不可思議。
“不貴了,想想我們由老遠跑來深圳,住星級酒店,還有星級演員做導師呢。”豪笑了。
“有用嗎?”子薇還是不服。
“有用!至少她們有事可做……唉!媽媽們也太閒了。”文光同意豪。
“上完課講話是客氣了。值得!值得!”豪似乎很有經驗。
旁邊一直低頭不語的憂鬱少女忍不住抬頭看他們。少女叫若然,來自澳門。但在一角低頭吃飯的少年卻沒有加入討論,他拿着小匙子把弄飯盒中的白飯。
“你叫什麼名字?”豪問。
少年沒有回話,仍舊自顧自地做事。
“我叫文光,她叫子薇,我們是來自佛山的,你來自何處?”
少年始終沒有抬頭,子薇又用普通話跟他說了一遍,同樣沒有反應。
“媽的!你也太沒有禮貌了!”豪發火了,搶走他手上的飯盒,並說了一連串的粗話,正想動粗。少年沒有抬頭,施施然往廁所方向走去,倒是引來了輔導員。
“天一來自香港。你們還有幾天相處時間呢,慢慢來,不用急……”工作人員說,然後朝男廁的方向走去。
三
午飯後,小菁回房午睡,想起少年們的傻笑,聯想到孩子剛學步時看到媽媽出現那一瞬的笑顏,不禁心花怒放。十七年前,小菁還是個二十歲的花季少女,為了愛情,為了愛情帶來的小生命,她毅然放下了求學的夢,遠離家鄉,與比自己年長廿歲的港商何潤男組織家庭。
“媽不是不尊重你……但女兒啊,你可是我們家的狀元呢。”面對豐盛的聘禮,小菁的媽媽流下了惋惜的眼淚。
“女孩子嘛!有才不如有貌,找份好工不如嫁個好老公。你家女兒才貌雙全,覓得如意郎君,多少女子求之不得呢。”身邊親友卻羨慕道。
可小菁的媽媽無法釋懷,那些年她也是班中學霸,可惜上初中不久就文革了,在看不到盡頭的運動中,她選擇了嫁人,復課時已為人母,錯過了求學之路。女兒是她唯一的希望,聰慧勤奮的小菁資質優厚,高考的時候以優異成績被香港的大學取錄,成為第一批赴港升學的內地大學生,可惜天意弄人,沒有想到女兒卻在香港遇上了愛情,而且還不小心有了身孕,誤了大好前程。
“女兒啊!你會後悔的……”小菁媽努力遊說她放棄孩子。但女婿下跪了,發誓只要生下孩子,小菁必定可以享福,到時候會僱傭人照顧孩子,老婆要讀多少書也行,去劍橋、哈佛升學也行!就這樣,小菁就當媽了,生孩子後,丈夫也守諾供養她,但小菁哪裡放得下孩子——嬰兒期寸步不離、幼兒期悉心照料、學童期讀書溫習……以為待到少年期,以天一乖巧聰明,終於可以放手了,萬萬沒有想到,向來品學兼優的天一竟然成了社運少年,不理父母的勸阻上街遊行。那一晚半夜未歸,警員致電請家長接回後,天一就沒有說過話了,他不上學,也不做事。小菁看在眼裡,痛在心中,心理醫生似乎也幫不上忙,後來丈夫不知從何打聽到這種專業親子培訓課程,就着小菁和孩子前往學習。把門窗關起來的孩子又怎會肯和母親去學習?大概是憐憫為他以淚洗臉、日漸消瘦的小菁吧。
“你再不肯去治療,我想比你早一步崩潰的大概是你媽。”心理醫生說服他。
天一並沒有恨父母,他放不下記憶中的烏煙瘴氣,還有那個在高樓上的身影。那個少年是天一最好的朋友,他們曾經並肩而行,為信念而戰。為此,好朋友與父母決裂,以死相迫。少年攀上高樓,以飛翔的姿態向世界招手,然後騰空……
“不要!啊……”天一向高空大叫,聲音卻沒有托住摯友,那小小的身影飛快着地,然後化作血紅大口一樣的食人花,把天一的靈魂吞噬了。天一在血泊中倒下,那一刻,他多麼渴望能像摯友那樣一睡不起,可命運弄人,他竟然醒來了,雖然有包容他的父母,可是他的靈魂彷彿隨好朋友遠去,他不要再聽到口號和呼叫,他甚至不想聽到這世間上所有的聲音;他也不想再看天空,因為舉頭就看到遠方的黑影向他招手,多少次,他期望隨好友一躍而下,可是他憐惜自己的父母,特別是那個為自己拋下夢想的媽媽,他覺得至少要為雙親活下去,所以無論多麼恐懼,他也願意同行。心理醫生說,他要的不是個別輔導,而是集體活動,他要重新面對和自己年紀相近、氣息健康的集體,才可以從好朋友自殺的陰影中走出來。因為情況特殊,課程安排了一位心理輔導員貼身照顧他。
“沒有事吧?”輔導員跑進廁所向正在嘔吐的天一遞上紙巾。
天一沒有接住紙巾,反而跑到水龍頭下洗臉和洗手,一直洗一直洗……洗了好久好久。
“你認識丁小菁女士,對嗎?”
天一還是不語。
“丁女士有點不舒服,託我來找他的兒子。請問你知道王天一在哪兒嗎?”
天一聽到媽媽的名字,很不情願地舉起雙手,然後隨輔導員的指示前行。輔導員給小菁發了個短訊交代細節,然後刻意帶天一走上高樓。天一起初害怕得站不起來,輔導員乘機攙扶着他,當他發抖的雙手握住了溫熱的手臂,感覺踏實了。
四
“同學們!早晨。”導師以充滿生命力的語氣向大家問好。
“早晨!”場內零星回報。
“怎了?未睡醒?昨天把自己的靈魂留在山谷內了?快呼喚回來!”
青少年們聽着笑了。經歷了一天上山下海的體力勞動,這群被家長視為“有問題”的年輕人,似乎有了神采。
這群孩子是問題少年嗎?也許不,他們只是喜歡打遊戲、談戀愛、不守規矩、不愛學習而已。平心而論,家長關心的不過就是最後一項吧,如果愛學習,前三項是可以適度調整的,問題是,孩子就是不愛學習才會愛上打遊戲、談戀愛吧?學習那麼美好,為什麼不愛?花了那麼多錢讓孩子學習,為什麼不好?學習可是攀越高峰唯一的路徑!這是師長們的套話,卻從來沒有人反思:我們給孩子的學習經歷真的美好嗎?花錢讓孩子學習真的開心嗎?那天,導師、攀山教練、輔導員等一行十多人,領着三十多位問題少年攀山去了。山路險要啊,有些少年體力差勁,根本就爬不動,由輔導員陪他們呆着;有的畏高,一往下看就哭了、發抖了,但也有隨教練拉着繩子頑強地爬上去的。登頂了!無限風光在險峰。在影片中看到自家孩子克服困難登頂的家長,臉上立刻掛上驕傲的笑容:“這孩子啊!還行!有膽識!可惜就是讀書不成。唉……”
“一天到晚打機不鍛煉,都說他沒有用……真不爭氣!”看着孩子沒能前進的家長歎氣了。
可沒有多久,鏡頭一轉,輔導員領着那群體力不行的孩子走山路。沒有險要的頑石,路好走多了,雖然途中停停走走,但最終還是登頂了。
“哎!我來啦。你們好辛苦啊……真笨!”走山路的孩子在頂峰遇見千辛萬苦登頂的孩子,竟然耀武揚威。
“哎呀!都是你們的錯!”攀石的孩子埋怨教練。
“哈哈!有時候啊,會選路真的很重要……我都說了,還是上國際學校好!”一位女士跟他身旁的丈夫說。
“不覺得自己好厲害嗎?那麼難走的路也登頂了。”教練笑了。
“厲害有什麼用?多費力!你看,人家輕輕鬆鬆還不是看到一樣的風景!”
“有用啊!那就證明了你厲害,那麼難的山都能登頂。你今天能攀越這山,明天就可以去攀另一座山,不是每座山都有路可走的。”聽到教練的鼓勵,攀山的少年開始回復了原來的自信。
“你們也要記住啊,不是每座山都有路走上山頂的,要多鍛煉自己。猜猜最重要的是什麼?”
“想放棄前要先看看還有沒有路!”一名走山路的少年笑了。
“再好的路也沒有用,她畏高!”子薇的母親歎氣了,“還是你家文光強!能徒手攀石,都說去祖廟體育會習武強。”
“小遊戲而已。這年代學武哪有用?天天打架不愛上學!還是你家子薇拉小提琴好。”
“唉!她現在補習班都不上了,還拉什麼小提琴?那天還恐嚇我,要是再迫她學,她會像新聞中的女孩,到音樂學校頂樓跳下來。嚇死我和她爸了,不學就不學吧。呸!都六級了,還差幾年就演奏級,錢白花了!”
“開開心心拉小提琴不就好了,考什麼演奏級。你家要求真高!”文光媽媽笑話她。
“子薇媽,看!我們家女兒。”若然母親說。
沒有上山的畏高少年們,並沒有一直坐在原地,輔導員帶他們去山下的林子摘水果,去河邊捉魚,玩得可開心呢。連平日整天愁眉不展的天一也開始觀察別人和幫忙摘果子。畏高少年的家長們看見自己的孩子在山下如此有成果,馬上露出欣慰之色。
不久,少年們在山下起點重遇,大夥看着“畏高團”找來的食物異常興奮,沒有人再笑話畏高的同伴無能了。影片中,畏高的子薇是個廚藝高手,幾下功夫就把魚洗切乾淨,燒得香噴噴的。
“看!你家子薇真行!”文光媽說。
“好好的小提琴不學,去烤魚?真是見鬼了。”子薇媽又好氣又好笑。
“別這麼說!廚藝也是藝術,澳門有一所高校在亞太區排名很高,可以培養出五星級酒店的總廚。學系收生要求很高,學成了可是不得了的專才呢。”若然媽媽自豪地說。
“你準備讓女兒去讀嗎?”文光媽問。
“我家女兒啊……得抑鬱症了。家裡只有她一個女兒……唉!我們家什麼都不缺,連廚師都請了,就算不讀書不工作,也夠她吃三輩子了,就缺一個會笑的女兒。”
“無事!無事!看看醫生就好!”子薇媽安慰她。
“啊!不要!”大家都聚精會神在操場的大熒幕時,樓底出現了一個人影,正跌跌撞撞地爬上欄杆。
“啊!不要!天一,不要!”天一媽媽一眼就認出了自己的兒子。她整個人崩潰了,發狂地跑到天一視線範圍內下跪:“天一,你要怎樣就怎樣,求你不要跳下來!媽媽愛你,你是我生命中的一切,求你下來!求求你!”
其他家長都看呆了,正準備上前安慰參扶,卻見到後面還有一群少年跟着走上欄杆邊緣。
“幹嘛了⁈孩子,下來!”眾家長都嚇壞了。
說時遲那時快,孩子們都舉起手上的飛機向高空拋,飛機在空中滑翔了一圈,最後如雪片落下,很輕很柔很美地着地……家長按導師要求把飛機拆開,字條中是某少年的筆跡:
我要高飛——心有多廣,就能飛得多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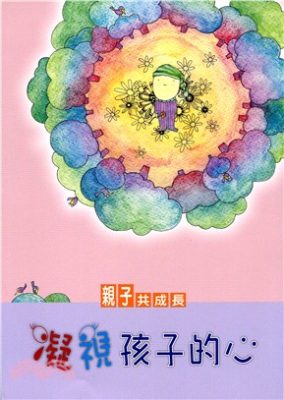



 《大叔的愛》日版及港版風潮席捲亞洲,好評不斷。從影視作品的角度,港版極盡幽默,日版唯美可口,均達至“吸眼球,搶收視”的效果。然而從教育角度,港電視台選擇在九點半時段播放該節目,卻讓作為家長的我有點憂慮。很多觀眾稱這是一個“純愛劇”,沒有意識不良鏡頭,然而,筆者以為,當中的“無別性戀愛觀”非常前衛,對傳統價值衝擊極大。
《大叔的愛》日版及港版風潮席捲亞洲,好評不斷。從影視作品的角度,港版極盡幽默,日版唯美可口,均達至“吸眼球,搶收視”的效果。然而從教育角度,港電視台選擇在九點半時段播放該節目,卻讓作為家長的我有點憂慮。很多觀眾稱這是一個“純愛劇”,沒有意識不良鏡頭,然而,筆者以為,當中的“無別性戀愛觀”非常前衛,對傳統價值衝擊極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