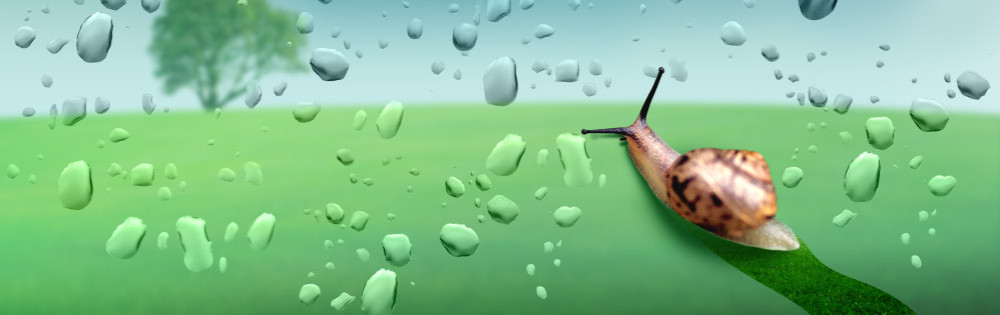一般喜歡種植的人都希望有一塊屬於自己的地,而我呢?卻是一個喜歡隨意栽種的人。
我從小就喜歡亂寫,那主要是因為我心裏有很多想法,卻不擅於講話。小學的時候,我沒有很多朋友,於是喜歡把話寫在日記本裏。有一天,日記竟然被人偷看了,其中一些內容還遭到了嚴厲的批評。由那天起,我發現日記不是個保險的載體,從此開始了漫長的文字放逐之旅。開心的時候,我寫下來,把文字當飛機飛放出去;傷心的時候,我有種自虐傾向──把寫下的東西連紙一起吃掉。朋友說,我這種愛好是神經病,但其實,裏面包含了我自以為不平凡的願望──把美好的東西傳出去,不好的則藏在肚裏。會不會因此中毒死掉呢?我一開始的確有點害怕,不過人傷心的時候大概也有死的衝動,吃著吃著,卻一直沒有死掉,證明有限的紙和墨水是人體可以承受的。這習慣一直到了初中,由於被老師發現了我喜歡寫,我便再也沒有空自言自語了。中學的時候,老師為我們指定了瓜菜的品種,且換得更大的收益。榮譽讓我變得受重視,卻失去了寫作最初的樂趣,當每個人都期待你可以種出更多更好的時候,會有一種駕馭不了的無力感。
為了逃避自己,又不至於無所事事,在沒有認真寫作的年月,我跑去辯論了。辯論是個很神奇的世界,那裡是沒有自己的。辯論的題目是抽籤決定的,立場的正反也不過是個隨機率。辯論討論著世界最關心的、最敏感的議題,前輩們常說,不要告訴我 “你覺得”,拿證據來。因為辯論,我開始認識世界,並克服了自己完美主義的習慣。厭惡辯論的人會說 “辯論是世界上最可怕的遊戲,因為辯論為辯而辯──圍繞抽籤的立場說違心話",但什麼是違心呢?當你還沒有深入了解一件事的正反觀點時,所謂的真心話,也不過是自以為是吧!在一次又一次的推翻和建構中,辯論成就了全新的我。但話語不是一種很踏實的載體──話音一落,如果沒法讓人明白,說了等於白說,就算是聽懂,思想也往往隨風而逝。別問人家能記住多少,有時候連自己都無法記起上一秒講過的話。
由思想最輕盈的載體回到文字,我經歷了很漫長的旅程。猶記得放棄寫作前,師長用心良苦的勸導 “趁著年青,基礎好、身段低就得多發表,等到一把年紀,文字功力肯定退化,你還好意思和小朋友一起寫麼?”到我想重拾筆桿時,的確要面對這種難堪的景況。文字功力可以重新練習,而 “面子”我也丟得起,於是就和學生相約投稿去,我每次都用不同的筆名,總希望有一個幸運地被掏起。有一段時間,我一股勁向各地各渠道發了些稿,一直石沉大海,不久就放棄了。反正只是自誤自樂,文字寫在哪都一樣,後來,流行寫網誌,我便開通了個人博客。由於剛生小孩,生活寸步難移,寫作便成為了我抒發情感的唯一途徑。朋友好奇,為什麼一個剛生孩子,工作繁重的老師可以如此 “多產”?其實很少人能夠理解,對於一個文字愛好者,閱讀和寫作比玩遊戲機和打麻將還要快樂!幸運地,我遇上了一位當作家的良朋,他經常鼓勵語文科組的同事創作,因為有了動力,我便經常發表作品,並在過程中,獲得了賞識──2011年1月,我終於擁有屬於自己的田地,可以讓更多人吃到我種的瓜果了。一個從來沒有想過死亡的人,是不會了解活著有多好,我是一個曾經放棄、曾經失去的人,所以,我比以前更了解擁有一片田地,可以定期暢所欲言的可貴。我不敢說自己比沒有地的作者寫得好,但我答應自己──每一次都得用心寫。 “斷章寫義”不是一個普通的寫作欄目,它需要以其他文章引入,起初我不太喜歡這種模式,覺得發揮受局限,慢慢地,卻又愛上了──能夠一邊積蓄養份,一邊抒發感受,可謂兩全其美。對於我這種總是 “想太多”的人,每周寫文章並不困難,但 “易寫難精”,如何把字數控制在800以內,而且文氣連貫、收束完整,是我最大的難題,因此我經常花比動筆更長的時間去刪改。
由隨處亂寫到有片小地,我仍然比較享受文字塗鴉的快樂。如果,寫作單純是為了自誤自樂,文字寫在哪裡的確是沒有分別的,但對社會呢?卻大有不同,那代表我在公共空間具有更大的話語權。如何從個人的自誤自樂,到感染他人,回饋社會,是專欄賦予作者的使命感。儘管我沒有能力像我的偶像魯迅那樣,為世界留下巨響,但依然能夠放飛夢想──我沒有再執著好與不好了,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世上沒有絕對的真理,我願意成為當中的一顆水珠,映出自己眼中的世界。因為習慣了辯論的思維模式,我人比較敢言,特別喜歡質疑和被質疑──當我想到一個題材,會先在面書和朋友討論,集合一些觀點,經過深入反思,再把想法寫成文章;發表過後,我也會把原文轉貼到面書上,聽聽不同人的意見,謀求反思和改善。我不需要把不好的東西藏在肚子裏了,因為我開始接受自己和這世界的不完美,我相信,在一次又一次質疑和被質疑的過程中,我們每個人都能夠自我完善!
親愛的讀者,希望你們有空去嚐嚐我種的瓜果,雖然未必是最甜美的!我叫鏏而(鏏:粵音 “睡”,漢語拼音 “ wei4”),一個比較幸運但沒有特別意思的名字。
文/鏏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