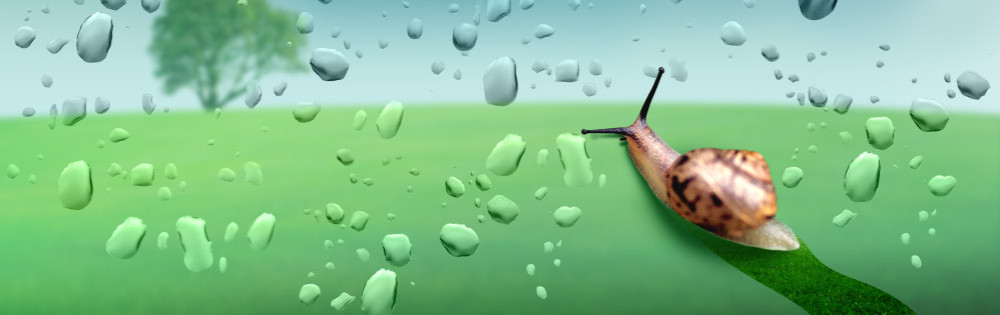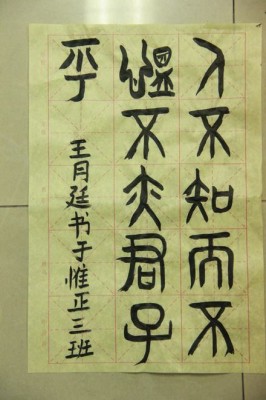我是一個異常冰冷的人,所以,一直希望找尋一雙異常溫暖的手。可惜,他不是!
他是冰冷的,由我第一天與他相約就知道——我們在網上相識半年,然後不約而同地去看一場舞台劇。儘管是相鄰,我坐在我的角落中思考,他坐在他的角落中大笑,笑聲像小王子那樣清脆悅耳,卻明顯沉溺於自己的世界。完場的時候,他走得很急,我想,一定有某朵玫瑰在某星球上等他吧。然後,我向他揮手,一如曾經被馴養的狐狸,依依不捨地送他,與他幸福的告別。
我準備把那堆一直想給他看的書,以郵寄的方式給他。其實我是明白的:“守望”的最終意義是“守”,而“望”可以站得很遠。他竟然冷冷地拒絕了我,“不好!那太沒意思了!”他在冷空氣中的回覆異常冷淡,及後卻燃起點點星火——“我本周買了舞台劇的票,鄰坐仍沒有人;下周要去的演唱會仍沒有伴……你到時候可以給我的。”“哦……”我始料不及,頓失方寸。
更始料不及的是,等不到舞台劇和演唱會,隔天,我們就約會了。站在亞馬喇前地的巴士總站,風吹得有點冷,而他來得有點遲,不,其實他沒有遲到,只是我早來了。“冷嗎?”他把自己很厚很厚的圍巾捆住我的頸,還有我的心。我暖得不能呼吸了,同時卻感覺到他的手在發抖。“你更冷吧。”我把圍巾還他,他冷淡地拒絕了,“我本來就冷,習慣了!”“哦!”我冷冷地回了一聲。其實“本來就冷,已經習慣”的人,不正是我自己嗎?基於同理心,我把自己那比較單薄的圍巾脫下來,說,“我們交換吧!”然後,空氣中揚起了溫暖的笑聲,以及我們共震的體溫。
“我們拍張合照吧!”我提議。沙灘很黑,而他自拍的技巧又很笨拙,最終只能拍下兩個黑影,彷彿只有兩雙閃亮的眼睛。不!還有他那閃着小王子般天真笑容的潔白牙齒。“我帶你去看我釣魚的地方,好嗎?”他提議。龍爪角的路太黑了,我下意識地拉着一隻溫暖的手,也許他也一樣,只見兩隻來自不同星球的手,在空氣中摸空了幾回,終於還是找不到溫暖的交點。也許,他習慣等魚兒自己上釣吧,如同我一直期待有人送來熱情的懷抱。
“今天真的好冷!”他說。兩個冰冷的人由黑沙徒步走到竹灣,怎麼可能不冷?然而,心仍是暖的——當你想起一個如此冰冷的人,仍然願意與你在冷風中並肩同行的時候;當你知道他明明家住路環,卻仍然願意趕去亞馬喇前地巴士總站出發的時候;當你了解喜歡垂釣的他,願意主動把你托在掌心的時候。
竹灣不同於黑沙,沒有廣闊的海岸線,海灣只是一個小小的驛站——供人和船休息的地方。我們的心停泊於此,可以抹走虛空的冷,樹蔭為我們擋住了寒夜的燈,然後,月色在石櫈的泥地上,畫下輕晃的連理枝——月光如黑夜的火,我們在火中取暖,他的懷抱仍舊冰冷,而冰冷的雙唇卻在我同樣冰冷的唇上鑽出了火……二○一五年最冷的一夜,我戀愛了。我依然是個異常冰冷的人,他也是。而我們卻竟然在冷空氣相互廝磨中生成了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