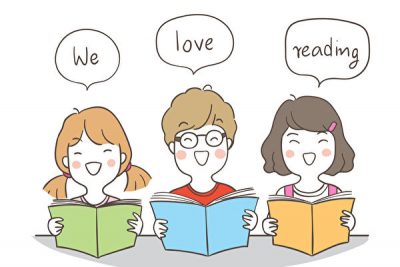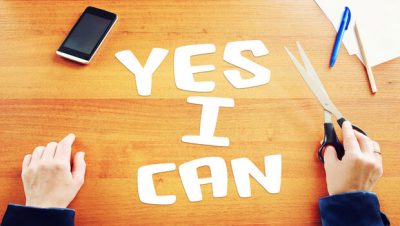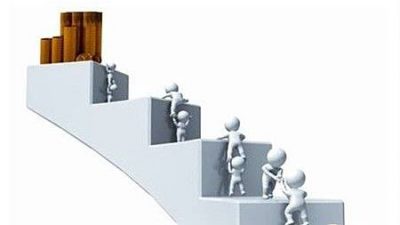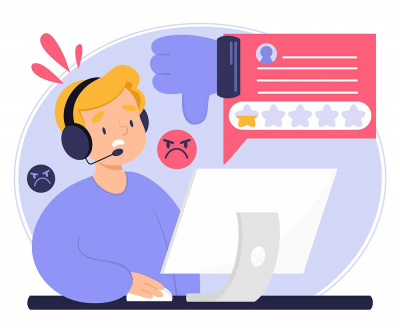
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話少誤事,言多有失。
【摘自:《假話全不說,真話不全說》,張鐵成著,新世界出版社,二○一○年十一月】
上周談到台灣“白飯之亂”的小風波。令我想起童話故事《國王的新衣》,只是主角不是尊貴的國王,而是平民飯店老闆。“熱炒店”向來宣傳白飯免費,約三十人的學生社團到店消費,卻被限量供應(營業時間到晚上十一時,晚上八時就說不再補飯,但游說學生自費下單炒粉麵等),學生不滿,吃完離開後在食評網負評“白飯供應不足吃不飽”,最後卻被老闆說成“點很少食物,吃了很多白飯,還要負評”。因為沒有“同理小商戶”,學生遭到網民鋪天蓋地的指責,不足兩星期已上升至檢討“公民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層次,連學校也出面要求學生道歉。
姑勿論免費供應白飯是否等於吃到飽,學生去“聲稱”有免費白飯的食店吃不飽,如實反映,有什麼問題?他們不過就是說出了事實,“說免費供應白飯的店令我吃不飽”,情況如同一個孩子說“國王沒有穿衣服”,世人覺得沒有穿衣服是可以的,那麼國王就沒有問題。真金不怕洪爐火,大家覺得“聲稱免費卻限量”是沒有問題,負評對店舖根本就沒有影響,到底為何要倒閉?說得底,無論食店還是學校,靠的都是自身實力,而不是那些三姑六婆的評論,但心理上,我們是拒絕接受不同價值取向的表態,認為這樣沒有教養,因為我們的處世觀強調:假話全不說,真話不全說。言多必失,溫和謙厚才顯得善良。
這真是我們想要的世界嗎?我感受到安徒生寫《國王的新衣》的心情,毅然寫下此文為學生打氣:孩子,能吃能睡不可恥!願你們放下“負評”,繼續真誠地做自己!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3-07/21/content_168924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