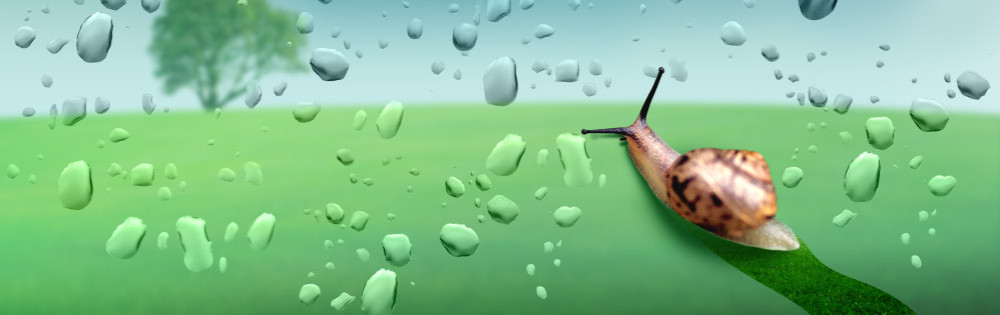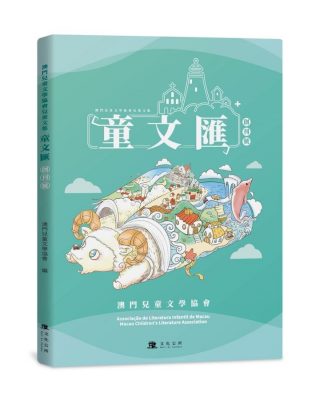
澳門兒童文學協會的說故事團隊,由本澳有經驗的說故事老師或兒童文學作家組成。為了提高讀寫教學的品質,協會邀請本澳公私立學校老師(在取得其任教學校同意的前提下)與兒童劇團,為年輕的協會成員示範讀寫結合的說故事方式。
【摘自:《童文匯》序;作者:向天屏;二○二三年十一月】
“近年澳門兒童文學發展蓬勃,希望你分享和介紹一下。”香港兒童文藝協會何紫薇會長向我發出邀請。“澳門兒童文學真有發展蓬勃?”我覺得汗顏。但文友說:“從後趕上,努力瘋長,也可以是很蓬勃吧!”於是我有了自信,並為報告做了個小簡介:
由孩子、教師、媽媽、義工、記者、作者、編輯、推手、研究員……一路走來遇到的困惑和喜樂為例,探索兒童文學的成長。
本來沒有什麼可以分享,但回顧一下,又覺得處處皆趣味,當中最值得分享的,大概是失敗的經驗和啟發吧。集合起來,活脫脫的就成了一個行動研究。其實,會友參與兒童文學協會的工作也一樣,我們有着不同的身份,為着不同的追求而來,最終目的是成長。至於要成長到什麼程度才叫“成功”?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定義。
《童文匯》終於出版了,不同於《童一枝筆》,那不是一本給孩子的刊物,那是一本讓寫作者、教育者、研究者全面了解兒童文學發展的綜合年刊。也許澳門不乏兒童適合看的素材,在協會部分學者的研究中,尋回了不少寶物,但為何當義工媽媽的時候,我們卻尋不到?因為我們缺乏一個正式的分類。未來,我們希望兒童文學不單單呈現在頒獎台和博物館中,還能夠在圖書館、學校、公園中唾手可得,並透過引文中說故事的團隊培養,發揮兒童文學應有的功能。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3-11/24/content_171695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