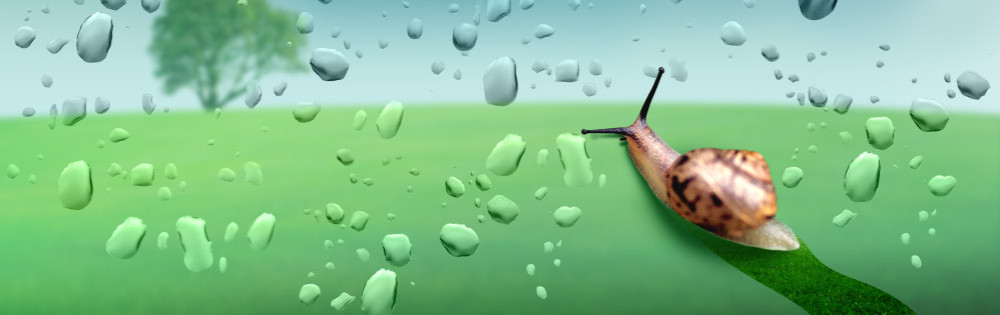未來的新文學將立足於人機協作的“新作者”,逐步完善由人類作者提供創意與構架、AI大語言模型算法深入分析並輸出文本、機器潤色、人工潤色等一系列“人——機——人”創作鏈條,創造(製造)出大量新文學作品(產品),呼應AI時代讀者的情感與想像,引領當代文學走向一個新的時代。
【摘自:〈AI時代未來文學創作新作者的三種可能〉,周艷艷、陳海,中國作家網,二○二五年一月十二日】
如同研究者所言,人機協作正改變文學創作。作為中年作者,我曾擔心會被新技術拋在後頭,直至聽到兒子說:“AI有什麼可怕?不用怎知好壞!”這句話啟發了我,於是開始探索不同AI的特色,發覺它們就像不同性格的朋友——POE像理科班學霸,文心一言像鄰家大姐,DeepSeek則是總把作業本擦破的文藝委員。在文學創作上,DeepSeek的文字更勝一籌,但人們很快會厭倦它的“AI式精美”。
回想我最初進文壇時,熱衷於寫詩,並非認為辯論人可以隨意變成詩人,而是渴望學習詩意,稀釋辯論腔。AI工具的出現,瞬間滿足了我由辯論人轉變為詩人的願望,這不是很好嗎?可惜,當美不再稀缺,其價值便隨之消失。當街頭充斥着魯迅和村上春樹的文風,讀者自然會感到厭煩。此時,我驚喜地發現,有讀者喜歡我原本的風格。
當AI式精美變得不可行,作者明明使用了這個工具,卻要花費巨大精力去淡化其痕跡,不如坦然承認“我在用”。一如當全網在追捧“吉卜力風”,而曾被宮崎駿嫌棄沒有畫畫才華的兒子卻堅定地說:“無人能取代我父親!”可見即使AI能模仿風格,但無法取代宮崎駿的思想與靈魂。未來,所有創作者面對的最大挑戰,或許不是如何超越他人,而是如何彰顯自我。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s://www.macaodaily.com/html/2025-04/11/content_182451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