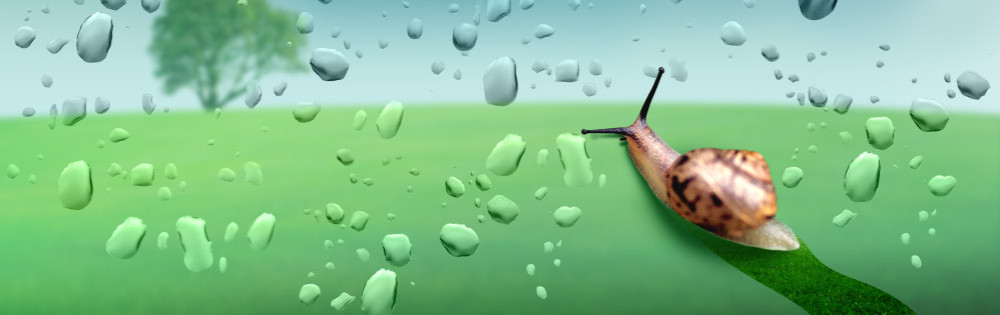你是自然之神手中的一張弓/幸福而謙卑地俯身/把箭矢般的孩子送向遙遠的未來/愛——是孩子的飛翔/也是你那彎曲而穩健的姿態。
【《論孩子》,作者:紀伯倫,柯倫-湖北譯,柯倫-湖北的博客,2011年12月】
記得第一次讀這首詩,我還在唸高小,當時讀的是冰心的譯本:
你們的孩子,都不是你們的孩子/乃是生命為自己所渴望的兒女。/他們是借你們而來,卻不是從你們而來/他們雖和你們同在,卻不屬於你們。/你們可以給他們愛,卻不可以給他們思想。/因為他們有自己的思想。/你們可以蔭庇他們的身體,卻不能蔭蔽他們的靈魂。……
作為孩子的我,極喜歡這首詩的上半截,大概是基於一種對家長的反抗:我由你而來,卻不屬於你!然而,對於詩的下半截:你們是弓,你們的孩子是從弦上發出的生命的箭矢。/那射者在無窮之間看定了目標,也用神力將你們引滿,使他的箭矢迅速而遙遠的射了出來。……其實我當時是讀不懂的,父母為何是弓?我又為何要等他們發射?自己的人生自己管。我當時這樣以為,一如今天輕狂的少年,總是覺得自己能撐起一片天。
直至有天,自己終於成為這一把弓,才開始感受到弓的重擔,因為孩子的成長往往在於家長一念:用力過輕,箭發不出去;用力過大,又會徒勞無功。這時候,我重看一次“你們的孩子,都不是你們的孩子,乃是生命為自己所渴望的兒女”有了一種釋然:既然不是屬於我,也不該由我去發射的吧。然而,沒有應不應該,這種相互依存的關係,彷彿是冥冥之中早已註定的。
年少之時讀此詩,我更多地看重了自由。為人母後再看此作,我更喜歡這位仁兄的譯本,因為他更重視為人父母付出的責任:你是自然之神手中的一張弓/幸福而謙卑地俯身/把箭矢般的孩子送向遙遠的未來……有些東西並不屬於你,但終歸是放不下的──那就是愛。
愛——是孩子的飛翔/也是你那彎曲而穩健的姿態。
原作
Your children are not your children.
They are the sons and daughters of Life’s longing for itself.
They come through you but not from you,
And though they are with you yet they belong not to you.
You may give them your love but not your thoughts,
For they have their own thoughts.
You may house their bodies but not their souls,
For their souls dwell in the house of tomorrow, which you cannot visit, not even in your dreams.
You may strive to be like them, but seek not to make them like you.
For life goes not backward nor tarries with yesterday.
You are the bows from which your children as living arrows are sent forth.
The archer sees the mark upon the path of the infinite, and He bends you with His might that His arrows may go swift and far.
Let your bending in the Archer’s hand be for gladness;
For even as He loves the arrows that flies, so He loves also the bow that is stable.
—Kahlil Gibran, The Proph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