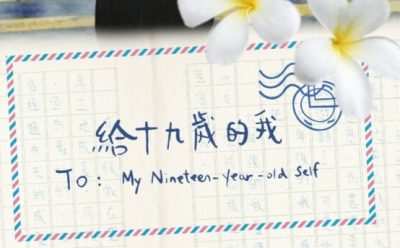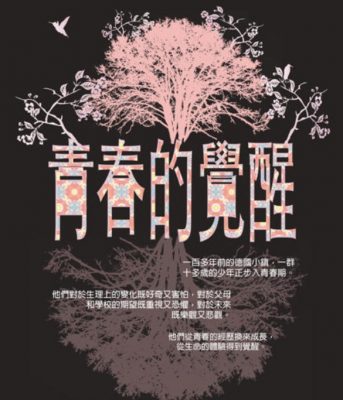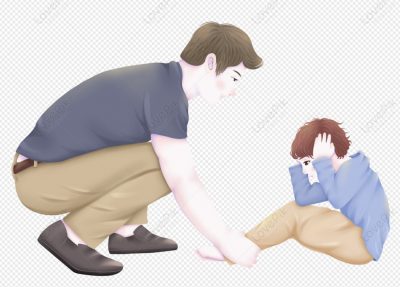切記分數是一定學習能力的體現,但只是固定知識而已,怎樣培養創新能力,而又能應付不同變化的挑戰才是學校必須迎頭趕上的任務。應試教育應該被拋棄,今後教給學生最重要的,是終身學習的能力和興趣,是素養和價值觀,其他交給機器做就行。
【摘自:〈為甚麼成績好的學生畢業後會變得平庸?〉,吳又可,二○二三年二月九日】
即使業界對其實際能力仍諸多猜疑,但在傳媒的吹捧下,ChatGPT以狂風掃落葉之姿席捲全球。有名校立即頒佈禁止學生用ChatGPT做功課的校規,問題是:在沒有現場監察的情況下,如何識別學生有沒有用呢?如果學生只是抽取部分元素,那又是否當抄襲?當中包含的種種技術、學術倫理等問題,似乎都無法找到合適的解決方案。
相對於教育界的憂心忡忡,我家○○後小子們反而表現得輕鬆自若:誰說抄襲功課一定得用ChatGPT?學生真的不想做,可以抄同學功課,請補習老師,甚至去某購物平台請人代筆……ChatGPT只不過比較方便。關鍵不是我們怎樣看待機械人所做出來的答案,而是如何看待功課的意義?功課是輔助自己學習的過程,而非應付老師和取得成績。再說,誰說“抄”一定就不能學習呢?那補習老師給我們的答案,算抄襲嗎?
雖然以上答案還有很多値得深入探討的空間,但明顯在智能產品下成長的孩子們,對新事物的接受程度更高。時代不一樣了,AI時代的人才需要的不再是死記硬背的技能,而是思考、判斷和決策的綜合能力。我們要嚴格打擊的,也許不是學生用ChatGPT,而是教師以傳統應試教學方法去評量自身“教學成效”的心態。我相信,“靈魂工程師”的角色是不會被取代的,當教師重視素養和價值觀教育的時候。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3-02/24/content_165612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