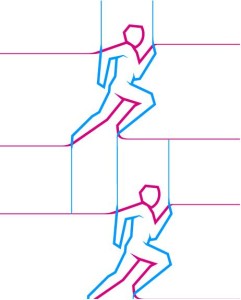澳門足球代表隊,在國際賽、地區賽、埠際賽上長期抱公平競爭心態,那麼,在這次一直以來像嘉年華般的交流中派出超齡(有指祇是大半歲)球員出賽,到底是有心出術,還是基於澳門本土風情的“圍威喂”心態,認為差唔多年齡上場玩吓都冇所謂?
【澳門體育版:敎練辭職疑點重重。澳門日報,二〇一三年十月十三日】
“與 世無爭,簡單平凡”是小城予人之總印象。由於地小人少,本澳在各項世界級競賽中均屬陪跑姿態,已經習以為常,很難想像,一項嘉年華性質的粵港澳靑年交流活 動,會動用作弊的方式求勝。事件一經媒體披露,社會各界嘩然。筆者由學生到敎師,參與學生課外活動幾十年,且曾就此作專項硏究,對此事感觸良多,故寫下本 文。
經一事,長一智,能夠在小事中碰壁,給來者借鑑,無論如何不是壞事。但事件尙未平息,隨即傳來九名敎練集體辭職的消息,姑勿論 辭職是誰的主意,不正視問題,改過自新,卻來個“斬腳趾避沙蟲”,讓孩子失去一批本地資深的足球敎練,實與“玉石俱焚”無異。其實,經常參與澳門大小競賽 的朋友,對澳門本土風情的“圍威喂”文化也習以為常,如:某大型體育賽事,賽會從不認眞核對參賽者身份,因而經常出現非該校學生頂替出賽的情況;某些學術 賽事輕率面對小節,連續數年出現技術錯誤。有一次,某比賽工作人員更當衆和筆者對質“小事啫,你作為老師,都斤斤計較,點敎好學生?”,即使最後願意接受 賽果,但只要提出任何建議,也足以招來閒話:“輸咗又唔服氣!無體育精神!”仿佛比賽除了接受結果,公平與否無關重要,而“志在參與”則又可堂而皇之地成 為賽會處事苟且,不重公平的美麗說詞。長久下來,情況如同過馬路看紅綠燈——精人衝燈,笨人苦等,在不重視公平競爭的情況下,違紀違規視為常態,一代一代 地根植“圍威喂”比賽文化。
眼不見,不為淨,足球敎練集體辭職無濟於事,只有社會整體的覺悟,重視“公平、公正、公開”的比賽文化,以至建立公平公義的社會氛圍,才能根治社會長久的核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