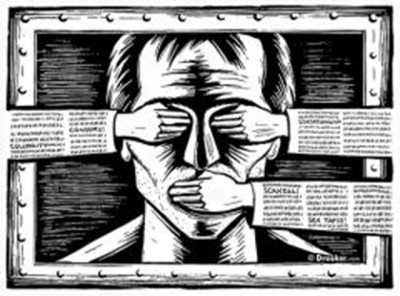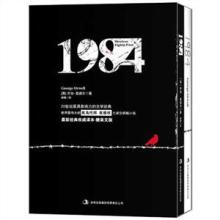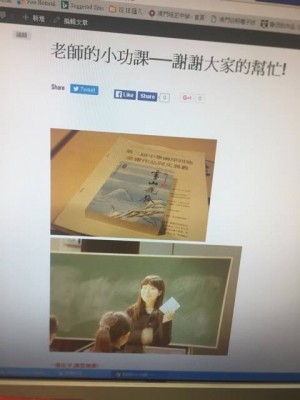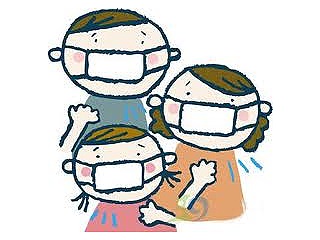十七歲,她遇見這位後來成為功夫巨星的他,二十七歲,他永遠離開她。十年歲月,對於每一個人來說,都難說長短,但這些影響了她的一生。對世人來說,她永遠是李小龍的妻子,他兒女的母親,他遺志的發揚者,除此之外,都不重要。
【摘自:網絡文章〈介紹李小龍的妻子義無反顧的背後女人〉,伊秀娛樂,2015年11月23日】
身在香港文化博物館最低層的咖啡館,心卻依然浮游在樓上影視展覽廳《李小龍風采一生》的紀錄片中。沒錯,那是“浮游”,因為巨星的光芒有一種沒有根的虛幻。
“小姐,你的維也納咖啡!”我望着桌上那杯精緻得不知從何喝起的飲品──白色的奶油花瓣樣的散着,一如睡蓮。
“攪拌一下就可以喝!”店員指導我。
然而,誰捨得攪拌呢?一如巨星的記憶,誰捨得讓他沉沒?不知怎地,有張臉一直在我腦際晃動,那不是李小龍,而是他唯一的結髮妻子蓮達 · 李 · 卡德威爾:“那年,我在跟他學功夫,他問我,要去太空針塔嗎?我說,是我們整隊人一起去嗎?他說,不是,就和你一個去!”;“那年,家裏經濟困難,他說去做保安員,我叫他別去,做保安員的男人將來怎麼在荷里活混?然後,我就去做接線生!”;“是的!他有很多女性朋友,大大方方帶回家,然後我們一起看他習武”……我仿佛看着她由十七歲的花季少女,一直走進而立之年的夢魘,然而,她的語氣仍是那樣淡然。也許全世界都因“李小龍死在別的女人床上”而替她不值,而她卻只記取了當中的甜。早年喪夫,中年喪子,對一個女人來說實在不容易。人生的悲歡離合,卻如她臉上的年輪,那樣堅定地支撐着一雙明亮的眼睛。
“要不要寫一張明信片給未來的自己?”同行的友人建議。我猶豫着打量桌前的咖啡──白花瓣融化了,泛起黑色的浮萍。我用小匙子攪拌數下,白和黑就分不開了。舉杯輕嘗,苦中帶甜,奶油的順滑揉成如絲的記憶,遂寫下本文,“記”給未來的自己。
附:本文記於2016年12月13日,順作小詩一首留念
#1213
用牛乳織成的花
總是會融的
無論底下剩著的是咖啡
還是茶
如果1314本身並不存在
那麼,1213也不錯了
至少能化作杯中的
柔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