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叔本華自己也曾說過:“辯論技巧與邏輯,是兩個完全不同領域的學問。”我們在知道這些技巧之後,只要不拿來為惡,偶爾用來捍衛自己的想法,也不是什麼罪惡的事;又至少,知道這些詭辯技巧,日後當遇到他人用這些方法來對付我們時,我們也能堅守立場,不至於被對方似是而非的說法牽着走,讓雙方可以再次回到理性討論的範圍中。
【摘自:《每一天都拉開差距》,許成準,大是文化,二○二一年九月】
你是“辯論女王”,家人一定很怕和你吵架!實情是我近年除了在臉書開題議事,及在真正的辯論比賽場合,平日很少和人辯論,即使是朋友主動和我討論,我也是點到即止。由辯手、教練到評判,辯論接近三十年,我並沒有覺得能言善辯無敵,反而學會了冷靜地處理分歧和攻擊。
家不是講理的地方,工作場所也不是人人有權講理。家人朋友不是你有理便認同你;領導同事不是必須認同你……既然都沒有用,何必學?學生會問。不是沒有用,只是不用於壓倒別人,要記住生活中沒有一個獎項叫“最佳辯論員”。很多人以為辯論人必然執迷,其實那只是誤解,辯論比賽的立場是抽籤決定的,長期的辯論訓練,會讓我們成為很好的寫手——手起刀落,什麼立場也可有理,然而,更大的收穫應該是明辨是非。也許我們都不能夠說服別人,但至少可以看清事實,不容易被迷惑。另外,因為習慣多角度思考,我們也比較少糾結於問題本身,如同《每一天都拉開差距》一書中,引述叔本華的名言:辯論讓我們學會在爭辯中脫身!
辯得好不如活得好,人生不是一場辯論比賽。新年伊始,我要特別勉勵自己,也藉此與讀者共勉。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2-01/07/content_1568779.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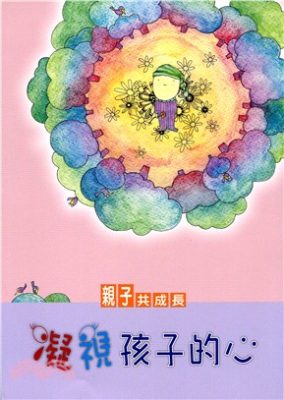



 《大叔的愛》日版及港版風潮席捲亞洲,好評不斷。從影視作品的角度,港版極盡幽默,日版唯美可口,均達至“吸眼球,搶收視”的效果。然而從教育角度,港電視台選擇在九點半時段播放該節目,卻讓作為家長的我有點憂慮。很多觀眾稱這是一個“純愛劇”,沒有意識不良鏡頭,然而,筆者以為,當中的“無別性戀愛觀”非常前衛,對傳統價值衝擊極大。
《大叔的愛》日版及港版風潮席捲亞洲,好評不斷。從影視作品的角度,港版極盡幽默,日版唯美可口,均達至“吸眼球,搶收視”的效果。然而從教育角度,港電視台選擇在九點半時段播放該節目,卻讓作為家長的我有點憂慮。很多觀眾稱這是一個“純愛劇”,沒有意識不良鏡頭,然而,筆者以為,當中的“無別性戀愛觀”非常前衛,對傳統價值衝擊極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