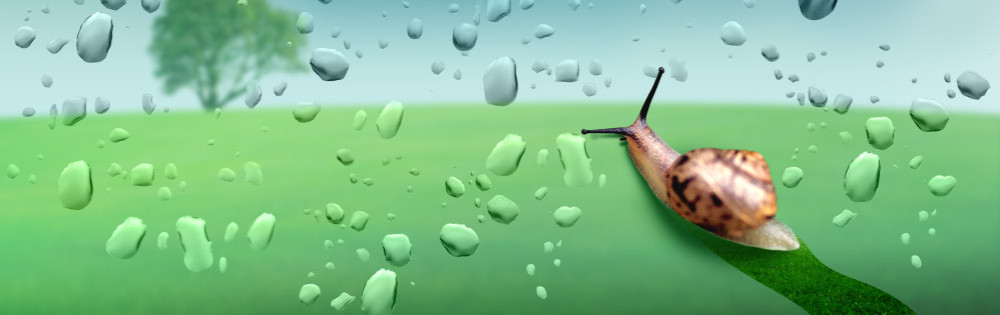你要明白,你是為興趣求學,但學生是被逼學習。所以教學情境的建構非常重要,教育戲劇在培養求知的快樂。
【摘自:“表演藝術在中小學課程的應用:創新教學及跨域實踐”第十七期兒童戲劇教育教師培訓班;講者李其昌(筆錄);二○二二年七月十九日】
在澳門疫情失守,小城進入“相對靜止”的一周,我參加了為期五天的線上課程。戲劇理論硬知識一下子是記不住的,表演技藝沒有系統操練恐怕也學不成,最有價值的學習莫過於觀念的更新。
作為兒童文學作家,湯素蘭老師在《我的兒童文學閱讀與寫作》中給我最重要的提醒:“作品的境界反映了作家自己的人生覺悟,除了藝術的創造力,還要提升精神的創造力。”而教育戲劇文化給我的“精神創造力”,關鍵詞是“平等、快樂、創意”。有別於精英主義,教育戲劇重視觀眾的感受和需求,需要放下孤芳自賞的權威標準回歸創作,才能感受童真,體會到“為孩子創作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
教育戲劇有別於戲劇教育,教育戲劇是用戲劇方法與戲劇元素,應用在教學或社會文化活動中,旨在學員參與,從戲劇體驗中領略知識的意蘊,從相互交流中發現可能性、創造力。過程中,我們需要包容和欣賞參與者的差異和獨特性,相信每個人都有能力感受戲劇活動的美好。李其昌老師在引文中的一段說話如雷貫耳,讓本為語文老師的我恍然大悟:孩子不是一隻知識的填鴨,培養求知的快樂尤其重要。
知易行難,五天密集課程給我們的養分不可能完全吸收,在完結的時候,我且記下李其昌老師的金句作為座右銘——由“坐中學”到“做中學”,我們就贏了!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2-07/29/content_161180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