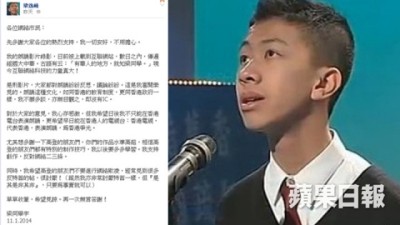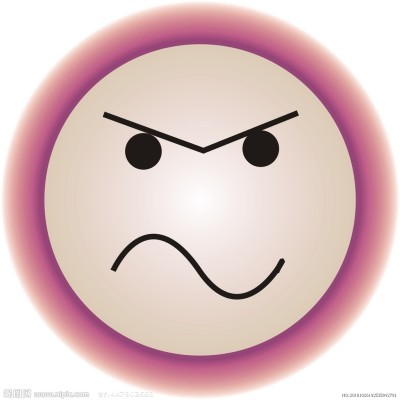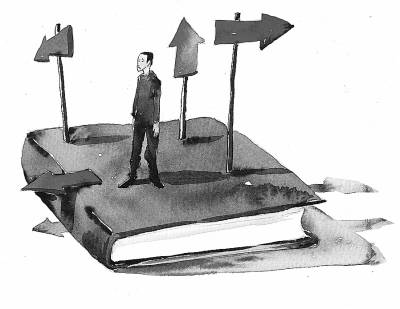我卻能理解為甚麼網友覺得他(香港學校朗誦節優勝者梁逸峰)可笑,只要打個比喩就較易明白,那就像用了流行曲的標準去批評粵曲。
【《梁逸峰的朗誦與 “狂舞派”的Rebecca》,作者:吳愛達,《評台》,二○一四年一月四日】
五度取得香港學校朗誦節冠軍的學生梁逸峰,其朗誦短片被網絡瘋傳,網友取笑其表情誇張做作,甚至進化為網上欺凌——風潮席捲港澳,進而橫掃內地。內地網友驚 異粵方言文化之 “奇異”,港澳朋友卻直指那是受“紅潮”(內地五四文化)之污染,各說各話,務求矮化別人,抬高自己。人們愛說 “如果我係孟浩然,聽到 都想死”,你若問他“孟浩然時代係點朗誦呢?”,他卻答不出來。
大家都努力擬造事件的趣味性,有人花時間“改圖配上粗俗字句”,有 人花精神錄製“奇趣短片”,有人甚至利用高科技製作混音版本,務求做到 “惡搞多樣化,嘲笑遍地開花”,就是沒有人願意用心了解古詩詞朗誦到底是何種文 化?其實古典詩詞的朗誦風格由來已久,因為粵語接近古韻,故當中又以粵方言朗誦最為正宗。 “風采中學中文科主任陳玉燕指出,朗誦本身是利用聲音、面部表 情及身體語言等建構詩詞篇章中的畫面,以幫助受衆感受作者希望帶出的情感及思想”(明報,二○一四),而梁同學重點被嘲笑的“望風景”,就是代入意境的表 現,而當中的所謂“誇張”,基本脫胎自粵劇神韻。根據本人對詩詞朗誦的基本認識,梁同學的表現屬正常,而門外人覺得“難頂”也屬常態,如同我當老師的年頭 硬着頭皮敎古詩詞朗誦,一樣覺得“難頂”。但我沒有排斥這種文化,親自去求敎高人,得多位名師指點,由腔調到句讀,由入聲到變調,終於慢慢地感受到深層的 意韻,對古典詩詞文化的領悟又有了進一步的升華。學戲劇的妹妹在戲曲藝術的訓練中,也有相同的體會。可見博大精深的表演藝術如陳年佳釀,要懂酒的人才能喝 出甘美。
“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在古詩詞朗誦的修煉中,眞正的內行人不多,外行人是願意一窺眞貌,還是執意矮化別人?是文化良性發展的關鍵。
文/ 鏏 而
後記:
真理未必越辯越明,但肯定有助思考,和文友第一次不約而同的”同台辯論”,值得紀念:
話說朗誦(凌 谷,澳日)
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14-01/10/content_869210.htm
“我以為,只要深入感受並理解詩文,盡量把情感起伏曲折清晰明白地表現出來,就是很優秀的朗誦。可是,一旦變成競爭意識強烈的比賽,一切都可能開始變質。就以太極拳為例,無論作為養生練氣還是自衛搏擊的,太極拳都是一套沖和流逸的內功拳,但它變成一種表演和比賽後,就成為大開大闔的華麗套路了。因為太細膩內歛的美感,識之者寡,更難標準化,很難定下指標。很可能不小心落入外行人手上,定下了體育專業所特有的指標,以致張三豐重生,也難入評判法眼。詩文的朗誦也是一樣,那些細緻入微的情感表達,往往不如誇張矯情的來得突出。”
本人認同比賽文化的弱點,不過其不獨為朗誦比賽,諸如:辯論,文學,戲劇,所有比賽都是標準爭奪戰,大家對輸贏不必看得太重呢!